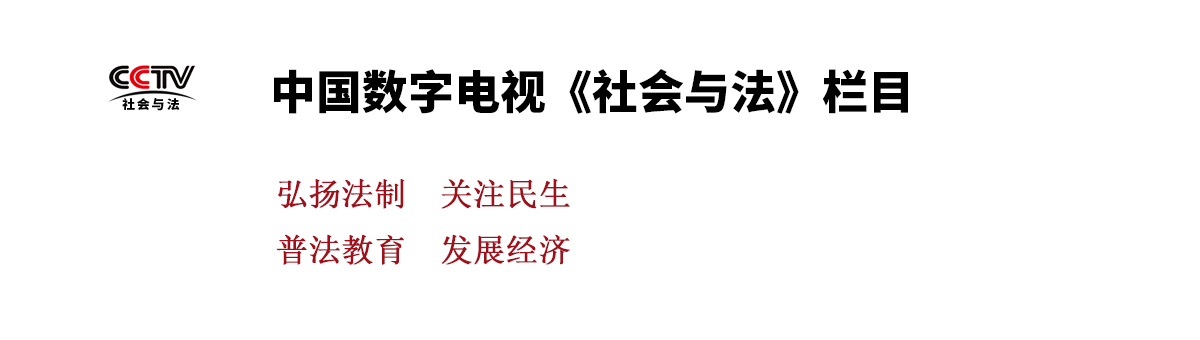嗒嗒……嘀嗒……嘀哩……哒哒……一阵清脆的起床号声把我喊醒,我慌忙起床穿衣,整装待发,恍惚间我又回到那魂牵梦绕的军营,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像这样恍惚间的举动和如此类似的梦幻,我记不清有过多少次了。
我离开可爱的军营已经30多年,可那里的一切还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忘不了那座落有序的苏式营房,虽不气派,也不宽敞,可住着舒服,冬暖夏凉;忘不了营区路旁一排排高大挺拔的白杨树,它像威武列队的士兵站立在哨位上,其不折不挠努力向上的精神给了我们勇气和坚强;忘不了营房旁边的那条小河,它似游蛇一般弯弯曲曲,流淌不息的河水唱着动听的歌,让人心情舒畅;忘不了山岗上的训练场,它原本是几座小山丘,是我们三营官兵一锹一锹挖出来的,我记得很清楚,那是1975年的冬季,天寒地冻,山丘上的土坚硬如铁,那时没有土方机械,我们只能发扬人定胜天的愚公精神,与天斗与地斗与己斗,经过一个多月的大干苦干拼命干,搬走了山丘填平了沟壑,马村兵营才有了如此像模像样的训练场……
当然,最让我忘不了是嘹亮的军号。军号是军人的魂。
翻阅历史画卷,我们发现人类自从有了军队就有了军号。军号可以号令三军鼓舞士气,也可以兴礼仪振国威。我军初建时期就有司号兵,连编有司号员,营编有号目,师团编有号长,编制在通信兵的序列中。那军号不是谁就能吹的,选拔号兵大有讲究。我当兵时的司号员都是精挑细选的,比选女婿还过细,新兵站成一排,副连长当考官,带着老司号员从左至右筛选,先看嘴唇,再看牙齿,厚嘴唇的不行影响发音;牙齿是关键,不整齐有缝隙易跑风漏气,同样不在选择之中。这两项过关了,再测试肺活量,留下胜出者,然后综合考量,保留一人,择优录取。
军号是军人生活的向导。最常见的军号有起床号,出操号,收操号,集合号,上课号,下课号,休息号,开饭号,午睡号,午起号,晚点名号和熄灯号等等。论军号种类,这只是冰山一角。曾当过司号员和号目的赵志言战友介绍,我军军号有勤务号,联络号,行动号,名目号,连队兵种号,战斗命令号和礼节号七大类,有200多个曲谱,具体曲目名称他也记不清。就部队而言有10多种常见号足矣,而司号人员训练的曲谱远不止这些,虽然不要求他们把200个曲谱都学会,毕竟多多益善,既要立足当前,又要着眼长远。可想而知,号兵的训练强度有多大。他们除参加营组织的日常训练外,每年还有三至五个月的团集中训练,每期集训就是一场历练,是一次次脱胎换骨的蜕变,每个人的嘴唇都肿了,破了一次又一次,连喝水吃饭都受影响,仍坚持练号。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,为了军号更嘹亮,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?
同众多战友一样,我对军号的认知经历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。刚入伍要进行三个月的新兵训练,主要科目有队列训练、体能训练和射击训练。初来乍到诸事开头难。艰苦的训练让我们疲惫不堪,浑身骨头就像散架一样难受;紧张的生活让人难适应,大脑好像有根弦紧绷着。在这种心理作用下,听到军号更紧张。难怪好多人说“老兵怕哨新兵怕号”。军号急促有力,震人心魄。新兵不懂号,号声一响心头突突乱颤,尤其是紧急集合号,让人紧张发怵。松是害严是爱,越害怕越紧张越需要强化训练。于是各连把紧急集合作为提高新兵快速反应能力的突破口,隔三差五的搞次突然袭击,通常在夜深人静时,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军号突然响起。按规定起床穿衣打背包要在不开灯无照明状态下进行,要求5分钟内全副武装赶到集结位置。疲惫的我们从睡梦中惊醒,手忙脚乱不知所措,有的衣服穿反了扣子错位了,有下铺人穿了上铺的鞋,还有的刚跑几步背包就散了……落伍者免不了挨批,就这个熊样还能打胜仗?负责新兵的连排长便有了惩罚我们的话语权。新兵们提心吊胆,熬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,有的甚至和衣而睡等着军号响。
枯燥无味的新兵集训终于结束了。在那段日子里,我眼中的军号是家中的闹钟,是学校的铃声,是大集体催社员下地干活的吆喝声。
军号伴随我由稚嫩走向成熟是新兵下班排之后。说不清从哪天开始,我对军号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近感,不论哪种号声我都喜欢听,总感觉那是一种凝聚与召唤,是军队正规有序的助推器,是军人勇往直前,不畏牺牲的精气神。嘹亮的军号动听悦耳,我在有规律的军号声中追逐梦想。一声号响,或许是一次早操,一次开饭,一次班务会,一次熄灯,自己的呼吸和脉搏渐渐与军号声同频共振。经过一次次的痛苦磨练,一次次的精神洗礼,我性格坚强了,举手投足越来越有“兵样”了,觉得自己将不再是独立的个体,使命如山啊,总有一种力量激励我奋勇向前。那年深冬,寒风凛冽,千里冰封,我们踏上了长途野营拉练的征途。那是一次精神与意志的磨炼,当时的口号是“练好铁脚板,打击帝修反。”队伍从河南林县入河北涉县沿太行山麓开进。通常每天午夜起床——吃饭——行军,上午12点左右宿营。一路艰辛一路坎坷,很多人双脚打满泡,老泡破了新泡又起,没人叫苦也没人掉队。那天晚上行军我实在太累太困了,走着走着一脚踏空掉进一个深坑里,左腿摔伤,疼得我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医生赶来了,经过简单处理后要把我送回驻地治疗。此时此刻汗水浸湿了衣衫,疼痛曼延着全身,瞬间我也有过放弃,有打退堂鼓的想法。这时前面传来嘹亮的军号声,这是“前进”的号音,真可谓“号兵鼓鼓嘴,千军万马跑断腿!”队伍临时休息时间过了,又要开拔了。我读懂了军号的旋律,它似乎在鼓励我:前进!前进!战士宁肯前进一步死,绝不后退半步生!我为怯懦一闪念而羞愧,婉言谢绝医生的关心,强忍着剧烈疼痛,用双脚丈量豫冀大地,完成了千里行程。我因伤痛没得到及时治疗和休息引发骨质增生,不得不手术治疗,至今我的左腿外侧仍有十公分长的刀痕。
军号声声伴我行,让我从一个雅气未脱的学生成长为一名少校军官。从军18年,军号响在哪里,我就战斗在哪里,千里奔袭演练,部队施工生产,对越作战,赴京戒严,我恪尽职守冲锋在前,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。感谢军号给了我勇气和力量。我可以自豪地说:吾已尽其所能,无愧于天无愧于地,无愧于养育我的父老乡亲。
军旅让军人和军号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没有了悦耳的军号声,时常会产生一种游子在外的孤独和恍惚,大凡当过兵的人似乎都有过这种感受,以至于一些战友常把“起床号”当作晨起问候语。一个副连长的故事让我好感动。他作开颅手术后昏迷不醒,其妻日夜守候他的身旁,流着泪不断呼唤他的名字,可他仍像婴儿般沉睡。他那曾当过兵的老父亲突然一下子想到了什么,跑出去买来了一盒空白磁带,托儿子的一位战友把部队起床号录来,这位老父亲把录音机放在儿子的床头,一遍遍地播放着。奇迹出现了,副连长紧闭着的双眼忽然间溢出了大颗大颗泪水。此后,老人每天定时播放起床号,漫长的两个月过去了,副连长终于醒了……这就是军号的神奇魅力,是军人与军号割不断的情结。因而我在想,如果有一天军号在我耳畔消匿,会是怎么样?我的生活还能像现在这般润泽,这样从容吗?
好在我是幸运的,上苍一直在眷顾我。虽然我已转业,早已离开了熟悉的军营,可那嘹亮的军号却一直伴随着我,不离不弃,似乎是结伴而行,更象是前生注定。
我转业的工作单位办公楼和住宅楼在同一个院子里,东侧和南侧均与部队接壤,近在咫尺。嘹亮的军号响彻军营,在周边上空回荡,我时时都感受到了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。军号声声,像是提醒我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。是啊,不能忘,也忘不了党和军队的教育与培养,我努力践行诺言,退役不退志,无论艰难坎坷,无论时光变迁,永远不变心中的信仰和精神底色。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,自我感觉答卷是合格的。
退休之后,我和老伴当了随军家属,四处漂泊,孩子走到哪我们跟到哪,无论在襄阳还是在武汉,或者在祖国的大西南,那军号声从未消逝过。军号声声入耳,让我精神振奋干劲倍增,因为我知道带好孙子料理好家务如同“巩固后方,”能让孩子解除后顾之忧,全身心地投入到国防事业中去。想想看,这是不是有点拥军支前的味道?
嘹亮的军号伴随我走过近50个春秋冬夏,它是我心中最美的音符,最动听的旋律,也是我生活中最好的知音。待我老去以后,希望能有人记住我曾经是一个兵,更希望能为我播放一次军号,让号声嘹亮些,悠长些……
责编:李志明